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南屯審計與確信會計服務推薦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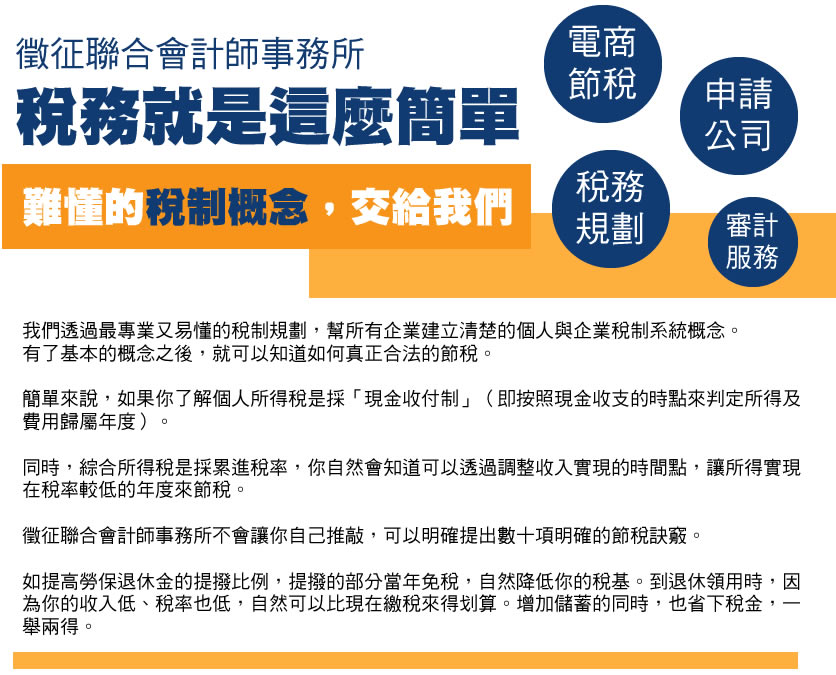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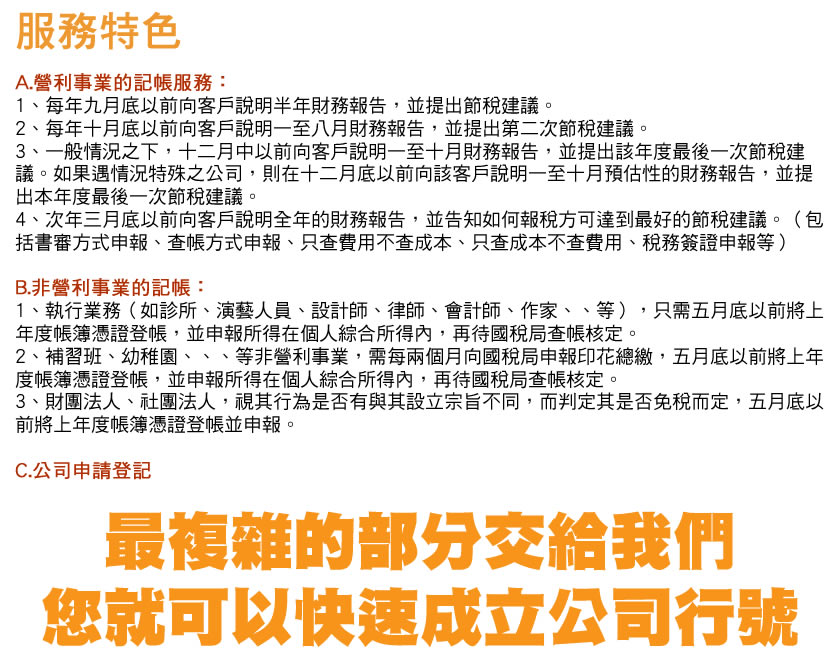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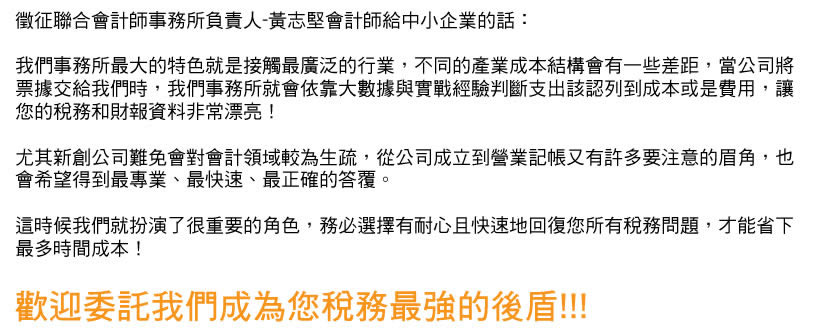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北屯電子發票b2b b2c諮詢, 台中北區BEPS與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VCM)諮詢, 台中西屯開公司節稅會計師事務所
生命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 許多同學應該都還記得聯考前夕的焦慮:差一分可能要掉好幾個志愿,甚至于一生的命運從此改觀!到了大四,這種焦慮可能更強烈而復雜:到底要先當兵,就業,還是先考研究所?我就經常碰到學生充滿焦慮的問我這些問題。可是,這些焦慮實在是莫須有的!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絕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毀了一個人的一生,也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救了一個人的一生。屬于我們該得的,遲早會得到;屬于我們不該得的,即使僥幸巧取也不可能長久保有。如果我們看清這個事實,許多所謂"人生的重大抉擇就可以淡然處之,根本無需焦慮。而所謂"人生的困境",也往往當下就變得無足掛齒。 我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從一進大學就決定不再念研究所,所以,大學四年的時間多半在念人文科學的東西。畢業后工作了幾年,才決定要念研究所。碩士畢業后,立下決心:從此不再為文憑而念書。誰知道,世事難料,當了五年講師后,我又被時勢所迫,出國念博士。出國時,一位大學同學笑我:全班最晚念博士的都要回國了,你現在才要出去?兩年后我從劍橋回來,覺得人生際遇無常,莫此為甚:一個從大一就決定再也不鉆營學位的人,竟然連碩士和博士都拿到了!屬于我們該得的,哪樣曾經少過?而人生中該得與不該得的究竟有多少,我們又何曾知曉?從此我對際遇一事不能不更加淡然。 當講師期間,有些態度較極端的學生會當面表現出他們的不屑;從劍橋回來時,卻被學生當做不得了的事看待。這種表面上的大起大落,其實都是好事者之言,完全看不到事實的真相。從表面上看來,兩年就拿到劍橋博士,這好像很了不起。但是,在這兩年之前我已經花整整一年,將研究主題有關的論文全部看完,并找出研究方向;而之前更已花三年時間做控制方面的研究,并且在國際著名的學術期刊中發表論文。而從碩士畢業到拿博士,期間七年的時間我從不停止過研究與自修。所以,這個博士其實是累積了七年的成果,或者,只算我花在控制學門的時間,也至少有五年,根本也沒什么好驚訝的。 常人不從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來看待生命因積蓄而有的成果,老愛在表面上以斷裂而孤立的事件夸大議論,因此每每在平淡無奇的事件上強做悲喜。可是對我來講,當講師期間被學生瞧不起,以及劍橋剛回來時被同學夸大本事,都只是表象。事實是:我只在乎每天二十四小時點點滴滴的累積。 拿碩士或博士只是特定時刻里這些成果累積的外在展示而已,人生命中真實的累積從不曾因這些事件而終止或添加。 常有學生滿懷憂慮的問我:“老師,我很想先當完兵,工作一兩年再考研究所。這樣好嗎?” “很好,這樣子有機會先用實務來印證學理,你念研究所時會比別人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可是,我怕當完兵又工作后,會失去斗志,因此考不上研究所。” “那你就先考研究所好了。” “可是,假如我先念研究所,我怕自己又會像念大學時一樣茫然,因此念的不甘不愿的。” “那你還是先去工作好了!” “可是……” 我完全可以體會到他們的焦慮,可是卻無法壓抑住對于這種話的感慨。其實,說穿了他所需要的就是兩年研究所加兩年工作,以便加深知識的深廣度和獲取實務經驗。先工作或先升學,表面上大相逕庭,其實骨子里的差別根本可以忽略。在“朝三暮四”這個成語故事里,主人原本喂養猴子的橡實是“早上四顆下午三顆”,后來改為“朝三暮四”,猴子就不高興而堅持改回到“朝四暮三”。(勵志 www.lz13.cn)其實,先工作或先升學,期間差異就有如“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原不值得計較。但是,我們經常看不到這種生命過程中長遠而持續的累積,老愛將一時際遇中的小差別夸大到生死攸關的地步。 最諷刺的是:當我們面對兩個可能的方案,而焦慮得不知如何抉擇時,通常表示這兩個方案可能一樣好,或者一樣壞,因而實際上選擇哪個都一樣,唯一的差別只是先后之序而已。而且,愈是讓我們焦慮得厲害的,其實差別越小,愈不值得焦慮。反而真正有明顯的好壞差別時,我們輕易的就知道該怎么做了。可是我們卻經常看不到長遠的將來,短視的盯著兩案短期內的得失:想選甲案,就舍不得乙案的好處;想選乙案,又舍不得甲案的好處。如果看得夠遠,人生長則八、九十,短則五、六十年,先做哪一件事又有什么關系?甚至當完兵又工作后,再花一整年準備研究所,又有什么了不起?當然,有些人還是會憂慮說:“我當完兵又工作后,會不會因為家累或記憶力衰退而比較難考上研究所?”我只能這樣回答:“一個人考不上研究所,只有兩個可能:或者他不夠聰明,或者他的確夠聰明。不夠聰明而考不上,那也沒什么好抱怨的。假如你夠聰明,還考不上研究所,那只能說你的決心不夠強。假如你是決心不夠強,就表示你生命中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其重要程度并不下于碩士學位,而你舍不得丟下他。既然如此,考不上研究所也無須感到遺憾。不是嗎?”人生的路這么多,為什么要老斤斤計較著一個可能性? 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一生背運:高中考兩次,高一念兩次,大學又考兩次,甚至連機車駕照都考兩次。畢業后,他告訴自己:我沒有關系,也沒有學歷,只能靠加倍的誠懇和努力。現在,他自己擁有一家公司,年收入數千萬。 一個人在升學過程中不順利,而在事業上順利,這是常見的事。有才華的人,不會因為被名校拒絕而連帶失去他的才華,只不過要另外找適合他表現的場所而已。反過來,一個人在升學過程中太順利,也難免因而放不下身段去創業,而只能乖乖領薪水過活。 福兮禍兮,誰人知曉?我們又有什么好得意?又有什么好憂慮?人生的得與失,有時候怎么也說不清楚,有時候卻再簡單不過了:我們得到平日累積的成果,而失去我們不曾努力累積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和別人比成就,而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最后該得到的不會少你一分,不該得到的也不會多你一分。 好像是前年的時候,我遇到一位高中同學。他在南加大當電機系的副教授,被清華電機聘回來開短期課程。從高中時代他就很用功,以第一志愿上台大電機后,四年都拿書卷獎,相信他在專業上的研究也已卓然有成。回想高中入學時,我們兩個人的智力測驗成績分居全學年第一,第二名。可是從高一我就不曾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音樂,書法,藝術和哲學,而他卻始終不曾分心,因此兩個人在學術上的差距只會愈來愈遠。反過來說,這十幾二十年我在人文領域所獲得的滿足,恐怕已遠非他能理解的了。我太太問過我,如果我肯全心專注于一個研究領域,是不是至少會趕上這位同學的成就?我不這樣想,兩個不同性情的人,注定要走兩條不同的路。不該得的東西,我們注定是得不到的,隨隨便便拿兩個人來比,只看到他所得到的,卻看不到他所失去的,這有什么意義? 有次清華電台訪問我:"老師你如何面對你人生中的困境?"我當場愣在那里,怎么樣都想不出我這一生什么時候有過困境!后來仔細回想,才發現:我不是沒有過困境,而是被常人當作"困境"的境遇,我都當作一時的際遇,不曾在意過而已。剛服完兵役時,長子已出生卻還找不到工作。我曾焦慮過,卻又覺得遲早會有工作,報酬也不至于低的離譜,不曾太放在心上。念碩士期間,家計全靠太太的薪水,省吃儉用,對我而言又算不上困境。一來精神上我過的很充實,二來我知道這一切是為了讓自己有機會轉行去教書(做自己想做的事)。三十一歲才要出國,而同學正要回系上任教,我很緊張(不知道劍橋要求的有多嚴),卻不曾喪氣。因為,我知道自己過去一直很努力,也有很滿意的心得和成果,只不過別人看不到而已。 我沒有過困境,因為我從不在乎外在的得失,也不武斷的和別人比高下,而只在乎自己內在真實的累積。我沒有過困境,因為我確實了解到: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絕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有劇烈的起伏。同時我也相信:屬于我們該得的,遲早會得到;屬于我們不該得的,即使一分也不可能增加。假如你可以持有相同的信念,那么人生于你也會是寬廣而長遠,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困境”,也沒有什么好焦慮的了。分頁:123
三毛:故鄉人 我們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墳的。 朋友坐輪椅,到了墓園的大門口,汽車便不能開進去,我得先將朋友的輪椅從車廂內拖出來,打開,再用力將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著他。他的膝上放著一大束血紅的玫瑰花,一邊講著閑話,一邊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時荷西在奈及利亞工作,我一個人住在島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兩星期便要我開車帶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歡去墓園,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園,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經上耶穌使他死而復活的那個信徒,墓園用這樣的名字也是很合適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個公墓里特別圍出了一個小院落,是給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國死者安眠的。其他廣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個小小的隔離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層一層的,有的是睡一塊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著另外一個先去了的朋友加里,兩個人又在做鄰居。 每一次將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時,他靜坐在椅上,我便踮著腳,將大理石墓穴兩邊放著的花瓶拿下來,枯殘的花梗要拿去很遠的垃圾桶里丟掉,再將花瓶注滿清水。這才跑回來,坐在別人的墓地邊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給我買花的錢很多,總是插滿了兩大瓶仍有剩下來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給放上幾朵。 那時候尼哥拉斯剛剛失去妻子沒有幾個星期,我不愿打擾他們相對靜坐的親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個人,自己悄悄走開去了。 我在小院中輕輕放慢步子走著,一塊一塊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塊白色大理石光潔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種,念到了一個金色刻出來的中國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頭十分清潔、光滑,而且做得體面,我卻突然一下動了憐憫之心,我不知不覺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陣默然。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這里,生前必是遠洋漁船跟來的一個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會成為孤墳。 我拿出化妝紙來,細心的替這位不認識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沒太多的灰塵的碑石,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 尼哥拉斯仍是對著他的太太靜坐著,頭一直昂著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輕輕走過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輪子邊,對他說:“剛剛看見一個中國人的墳,可不可以將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給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說:“多拿幾朵好!這位中國人也許沒有親人在這兒!” 我客氣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給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著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對他說:“曾先生,我們雖然不認識,可是同樣是一個故鄉來的人,請安息吧。這朵花是送給你的,異鄉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親人吧!”“如果來看露斯,必定順便來看望你,做一個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過幾次墓園,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輕輕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會兒,才推著尼哥拉斯回去。 達尼埃回來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們四個人去墓地便更熱鬧了些。 大家一面換花一邊講話,加里的墳當然也不會忘記。一攤一攤的花在那兒分,達尼埃自自然然的將曾先生的那份給了我。 那一陣曾先生一定快樂,因為總是有人紀念他。 后來我做了兩度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曾先生的確是來謝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來謝我,我歡喜了一大場。 以后我離開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個島上去居住,因為荷西在那邊做工程。 曾先生的墳便沒有再去探望的機會了。 當我寫出這一段小小的故事來時,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灣的親屬看到。他們必然因為路途遙遠,不能替他掃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島上居住,聽說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親屬有什么東西,想放在他的墳上給他,我是十分愿意代著去完成這份愿望的。 對于自己的同胞因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遠,接觸的機會并不多,回想起來只有這一件小小的事情記錄下來,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記 上面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寫的,為了趕稿,很快的交卷了。 這件事情,寫完也忘記了,因為文短。 過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聯合報》,在副刊室內碰到編輯曼倫,她說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報上發表的短文。 曼倫翻遍了資料,找不到刊過這篇文章的事實。其實,它當時發表在《中華日報》上,并不在《聯合報》。“有人打電話來報社,說三毛寫過一個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國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蹤了多年的兄弟,聽說在西班牙失蹤的,你有沒有這個記憶?”曼倫問我。 我很快的將在西班牙認識的中國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確沒有一個姓曾的。 我告訴曼倫,大概弄錯了,沒有姓曾的朋友,也沒聽說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蹤的中國人。 沒有想起這篇文章,他們在找的是一個失蹤的兄弟,我完全沒有聯想。 過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報社轉來的信,拆開來一看,里面赫然寫著曾君雄的名字,當我看見這個全名出現了時,尖叫了起來:“他家屬找的原來是這個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還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屬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來的信,曾先生的兄長和弟弟,要答謝我,要我去高雄講演時見見面,要請我吃飯,因為我上了他們兄弟在海外的孤墳。 面對這樣的一封信,我的心緒非常傷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給他家人報了這個死亡的消息?是事實,可是他們心碎了。 見了面,我能說什么?那頓飯,曾家人誠心要講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結果,我沒有再跟他們連絡。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納利群島去。一個酷熱的中午,我開車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墳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www.lz13.cn)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個島嶼,請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屬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會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復生,曾先生的家人,我們只有期望來世和親人的重聚。那個墓,如果您們想以中國民間的習俗,叫我燒些紙錢,我可以由台灣帶去,好使活著的人心安。 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請看見這篇后記的南部朋友代為留意,如果有認識曾家的人,請寫信到皇冠出版社來與我連絡。謝謝! 上墳的事,不必再掛心了,我一定會去的。 三毛作品_三毛散文集 三毛:我的寫作生活 三毛:高原的百合花——玻利維亞記行分頁:12
徐蔚南:山陰道上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的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崗。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的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里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里,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的兩壁墻上,常有人寫著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才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了望四周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鑒。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的永久秘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群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向導,最后的是一排瘦膺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里,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里。……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著河水的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只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與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的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的友誼已無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里的山崗,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云霧罩著了,巍然接連著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里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的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里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卻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蔽。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只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台,上面鋪著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游戲性質,盡情發泄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的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啊!多么活潑,多么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著那青空里的白云。白云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www.lz13.cn)地如棉花。一卷一卷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秘最美麗最復雜的畫片,只有睜開我們的心靈的眼睛來,才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的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云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它漸漸向山后落下,一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里。這時它的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淡了,云也暗淡了,樹也暗淡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的影子。 蒼茫暮色里,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匆匆回去。 徐蔚南作品_徐蔚南散文集選 徐蔚南:香爐峰上鳥瞰 王了一作品_王了一散文集選分頁:123
ACC711CEV55CE
台中中區會計、稅務及薪資委外暨相關之人力資源管理會計服務推薦
半導體製造與通路產業節稅方式 台中北屯電商稅務諮詢 有沒有可以節省營業稅的方式?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